
文/道堅
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明確記載巴國“其屬有濮、賨、苴、奴、夷、蜑之蠻”,這一記載揭示了巴國并非單一族群政權,而是以核心統治族群為中心,融合多個土著與附屬族群形成的多元聯合體。這些族群在巴國疆域內各有分布、各擔其職,既保持獨特文化基因,又通過長期互動形成共生格局,共同塑造了巴文化的豐富內涵。本文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,對巴國屬下主要族群的分布、特征及互動關系進行系統探討。
巴國屬下核心族群的分布與文化特質
巴國屬下族群多因地域、生計或習俗得名,分布于今川渝、鄂西、陜南、黔西北的廣袤區域,形成“沿江聚居、邊境設防”的空間格局,各群體文化特質與生存環境高度適配。
(一)濮人:巴地土著核心與農業基石
濮人是巴國境內分布最廣、人口最多的“第一大族”,因來源復雜且分支眾多被稱為“百濮”,既有世居巴地的古老部族,也有從周邊遷徙而來的支系。其分布以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三江匯流處為核心,今重慶合川、涪陵及四川宜賓一帶是其聚居中心,這一區域水網密布、土壤肥沃,為濮人發展農業提供了天然條件。
作為巴國農業與手工業的核心承擔者,濮人創造了成熟的稻作文明,合川唐家壩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,印證了其作為當地早期農耕開創者的地位。制陶與制鹽是濮人手工業的代表,沙梁子遺址出土的夾砂灰陶、紅褐陶罐釜,帶有繩紋、網格紋等典型紋飾,展現了其精湛的制陶技藝;而遺址中發現的陶質鹽鍋殘片,則佐證了文獻中合川“蒲子鹽”為濮人所制的記載。在文化習俗上,濮人流行崖葬與懸棺葬,信仰體系獨特,部分文化元素通過后世仡佬族(濮人直系后裔)的“祭濮王”儀式得以延續。
(二)賨人:軍事支柱與巴語核心載體
賨人又稱“板楯蠻”,因作戰時以木板為盾得名,是巴國最具戰斗力的族群分支,其聚居區集中于嘉陵江中游、渠江兩岸的川東北地區,今四川達州、巴中及重慶萬州一帶為核心區域,《輿地紀勝》明確記載“巴西宕渠,其人勇健好歌舞……古之賨國都”。
賨人的核心價值在于其軍事力量,《華陽國志》稱其“天性勁勇”,早在周武王伐紂時便作為先鋒參戰,以“歌舞以凌殷人”的戰前儀式彰顯斗志,后又助漢高祖定三秦,因功獲“戶歲出賨錢口四十”的優待,被稱為“白虎復夷”。作為巴國軍事核心,賨人語言成為巴語的主導形態,聲調豐富且軍事、狩獵術語發達,與今藏緬語族的羌語、彝語存在詞匯同源性。考古發現顯示,達州羅家壩遺址出土的柳葉劍、弩機等青銅兵器,印證了其“尚武”特質。值得注意的是,學界對賨人與廩君巴人的關系存在爭議,部分文獻認為二者同源,但《后漢書》《通典》等均將“板楯蠻”(賨人)與“廩君蠻”分段記載,證實其為獨立族群。
(三)苴人:巴蜀交界的文化中介
苴人是巴人分支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的族群,屬百濮支系,其名稱源于聚居的“苴地”,核心分布區在今四川廣元與陜西漢中交界地帶,地處巴、蜀兩國邊境,是巴國西部的戰略屏障。這一地理位置使苴人天然成為巴蜀文化交流的中介,其文化呈現鮮明的“二元融合”特征:器物既有巴人青銅劍的凌厲風格,又兼具蜀國陶器的細膩紋飾,廣元昭化遺址出土的器物充分印證了這一特質。
苴人與巴國的關系經歷了從附屬到疏離的轉變。初期作為巴國屬民承擔邊境防御職能,后因巴、蜀爭奪資源轉而與蜀國結盟,最終在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之戰中率先被攻占,其族群逐漸融入秦文化體系。文獻記載“儀貪巴、苴之富,因取巴”,可見苴地的富庶與戰略重要性,而其“通巴蜀之語”的文化優勢,也讓巴國農業技術得以借助苴人向蜀地傳播。
(四)奴人:南部邊緣的濮系分支
奴人是巴國南部的小型附屬族群,記載相對匱乏,推測為濮人分支或西南土著后裔,主要分布于今重慶南部綦江、南川及貴州北部遵義、銅仁一帶,與濮人聚居區重疊但處于文化邊緣。因人口較少且社會發展程度較低,奴人對巴國保持松散從屬關系,僅需繳納糧食、獸皮等貢賦,未深度參與巴國核心事務。
從文化特征看,奴人以原始農業與漁獵為生,器物風格與濮人高度相似但工藝更為簡樸,未形成獨立的文化標識,可視為“濮人文化的邊緣形態”。由于缺乏專屬考古遺址,其歷史軌跡主要通過地域文化遺存推斷,后世該區域仡佬族方言中保留的獨特詞匯,可能是奴人語言的殘存痕跡。
(五)夷人:東部邊境的多族泛稱
“夷人”并非單一族群,而是巴國對東部邊境多個土著群體的泛稱,分布于今湖北恩施、宜昌及重慶東部區域,與楚國接壤。這一群體構成復雜,既包含濮人分支,也涵蓋受楚文化影響的土著部族,形成“巴楚交融”的文化特色。
靠近巴國核心區的夷人部族使用巴語方言,向巴國繳納貢賦;而邊境地帶的夷人則頻繁與楚國互動,器物中出現楚簡文字風格的刻畫符號,甚至吸收楚語詞匯。巴國滅亡后,部分夷人融入楚文化,其余則演變為漢魏時期“五溪蠻”的重要組成部分,成為后世土家族的先民之一。其懸棺葬習俗與濮人一致,而祭祀儀式中又融入楚地巫風,展現了邊緣族群的文化適應性。
(六)蜑人:水域生態的適應者
蜑人又稱“蜒人”“蛋人”,屬百濮支系,是長期生活在水域環境中的“水上族群”,主要分布于巫巴山地及清江流域,沿長江、嘉陵江、烏江兩岸散居,以重慶涪陵、萬州及湖北宜昌為聚居密集區。漁獵與航運是其核心生計方式,巴國向中原進貢的丹砂、魚鹽等物資,多由蜑人通過水路運輸。
蜑人語言與其他族群差異顯著,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,詞匯中“船”“魚”“水神”等水上生活術語占比極高,與今壯族、侗族語言存在淵源。文化上,蜑人以船為家,住“干欄式”船屋,信仰水神并盛行“祀龍”儀式,其“民風彪悍”的特質使其在巴國水上防御中發揮重要作用。后世“疍家人”即為蜑人后裔,延續了其水上生活的文化基因。
族群互動:從多元并存到文化共生
巴國屬下族群并非孤立發展,而是通過資源爭奪、軍事協作、文化交流形成復雜互動網絡,最終構建起“核心主導、邊緣協作”的共生體系,推動了巴文化的形成與發展。
(一)資源爭奪與政治整合
巴國族群互動的初始動力源于資源分配。濮人占據的三江流域耕地與鹽礦,成為巴人核心族群與賨人西遷的重要目標,早期“巴濮鄰國,室家相賊”的沖突傳說,印證了資源爭奪的激烈性。但巴國統治者很快建立起有序的資源分配機制:濮人專注農業與制鹽,賨人承擔軍事保衛,蜑人負責運輸,苴人掌控邊境貿易,通過各司其職實現資源高效利用。這種分工模式使巴國形成“鹽糧為基、軍事為盾、航運為脈”的經濟體系,為其存續提供了保障。
(二)軍事協作與族群認同
軍事需求是族群凝聚的重要紐帶。賨人作為核心軍事力量,不僅承擔對外征戰任務,還與濮人、夷人組成聯防體系:濮人提供后勤補給,夷人負責東部警戒,蜑人保障水上通道安全。周武王伐紂、抵御楚國等重大軍事行動中,均能看到多族群協同作戰的身影。長期軍事協作促進了文化認同的形成,賨人信仰的白虎圖騰逐漸傳播至濮人、夷人群體,而濮人的稻作技術也被賨人、苴人廣泛采用,這種文化共享強化了族群向心力。
(三)語言交融與文化互滲
語言互動是族群融合的核心表現。以賨人語言為基礎的巴語成為族群交流的“通用語”,濮人、苴人語言中大量吸收軍事、行政術語,蜑人、夷人則在貿易詞匯中融入巴語元素。同時,文化習俗的互滲現象普遍:濮人的制陶技藝傳入苴人區域,賨人的“巴渝舞”被其他族群效仿,蜑人的水上祭祀儀式影響了沿岸濮人。這種交融并非單向輸出,而是多向互動——巴人從濮人處習得稻作技術,從蜑人處掌握航運經驗,最終形成“你中有我”的文化格局。
族群歸宿:融合中的文化傳承
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后,巴國政權消亡,但屬下族群并未隨之消失,而是通過三條路徑完成歷史轉型:一是融入華夏文明,賨人、苴人因靠近中原,在秦漢郡縣制推行中逐漸漢化,其語言習俗多被中原文化吸收;二是形成新的族群共同體,濮人、夷人等與其他部族融合,成為漢魏時期“五溪蠻”的主體,宋代以后逐步演化出土家族;三是保留族群特質,部分濮人、蜑人遷徙至西南山區,發展為仡佬族、疍家人等少數民族,延續了古老文化基因。
現代基因研究為族群傳承提供了實證:四川羅姓家族的基因檢測顯示其遺傳標記C-MF215856為賨人七姓后裔,2500年來未改籍遷徙,印證了賨人并非完全消失,而是以漢化形式延續血脈。而仡佬族的“折齒”習俗、土家族的“巴渝舞”遺存、疍家人的水上生活方式,共同構成了巴國族群文化的活態見證。
結語
巴國屬下的濮、賨、苴、奴、夷、蜑等族群,以三江流域的地理格局為依托,形成“各有側重、協同共生”的族群生態。濮人的農耕文明奠定經濟基礎,賨人的軍事力量保障生存安全,苴人的文化中介促進交流融合,蜑人的水上技能拓展發展空間,夷人與奴人則充實了邊緣治理體系。這些族群在數百年的互動中,既保持了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化特質,又通過沖突與融合凝聚成巴文化共同體。
秦滅巴國后,這些族群雖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,但他們創造的文化基因并未湮滅,而是融入華夏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,成為西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源頭。深入探討巴國屬下族群的歷史,不僅能厘清西南民族演化的脈絡,更能為理解中華文明“多元融合”的特質提供典型樣本。
(作者簡介:道堅,詩人、作家,重慶市九龍坡區人大代表、重慶市少數民族促進會副會長、曾任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中國政法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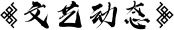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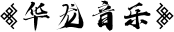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