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道堅
巴、蜀、苴三國是戰(zhàn)國時期西南地區(qū)的核心政治力量,其關(guān)系演變深刻影響了西南地緣格局乃至秦國的統(tǒng)一進程。蜀國作為核心大國,地域遼闊,無法實現(xiàn)有效控制,便分封同宗苴國以扼守戰(zhàn)略要沖;苴國在秦國巴國之間,作為蜀國的戰(zhàn)略緩沖地帶,借勢崛起后轉(zhuǎn)向聯(lián)合巴國抗蜀,形成“蜀強、巴峙、苴叛”的三角制衡;最終三國均因秦國戰(zhàn)略入侵而覆滅。本文結(jié)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(fā)現(xiàn),梳理三國關(guān)系的發(fā)展脈絡(luò),剖析地緣博弈的內(nèi)在邏輯,揭示其在秦漢大一統(tǒng)進程中的歷史意義。
一、分封制下的蜀苴同源與巴蜀并立
巴、蜀、苴三國的地緣格局奠定于西周至春秋時期,其初始關(guān)系由族群淵源、地理環(huán)境與政治制度共同塑造,呈現(xiàn)“蜀為核心、苴為藩屬、巴蜀并立”的基本態(tài)勢。
蜀國作為西南地區(qū)的文明核心,起源可追溯至蠶叢、魚鳧時期,至開明氏九世杜尚統(tǒng)治階段達到國力鼎盛。其疆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,北抵漢中盆地,南及云貴北部,憑借發(fā)達的農(nóng)耕文明與青銅技術(shù)成就西南霸業(yè)。巴國則聯(lián)合秦楚,攻破庸國,得濮人故地,收編武陵蠻族,形成以今重慶為核心,活動于川東、渝東北及鄂西一帶,受地理條件限制以漁獵與鹽業(yè)為經(jīng)濟支柱,形成與蜀國迥異的文化體系。《尚書·牧誓》記載,巴、蜀均參與周武王伐紂之戰(zhàn),作為并列的“友邦冢君”出現(xiàn),可見兩國早期并無明確從屬關(guān)系,而是同為周王朝分封的南方諸侯。
苴國的建立則源于蜀國的分封制度。公元前368年,蜀王杜尚滅亡昔阝、平周二國后,封其弟杜葭萌為漢中侯,在今四川廣元昭化區(qū)建立苴國,都城設(shè)于吐費城。這一分封兼具戰(zhàn)略與政治雙重考量:地理上,苴國控制金牛道入川咽喉,北接秦國漢中郡,南扼蜀中門戶,成為蜀國抵御北方威脅的軍事屏障;政治上,既通過分封宗親鞏固對川北氐羌聚居區(qū)的統(tǒng)治,又可避免王室內(nèi)部權(quán)力紛爭。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印證了苴國的藩屬性質(zhì)——廣元出土的戰(zhàn)國青銅戈鑄有“苴侯”銘文,其器物形制與蜀國金沙遺址同類器物高度相似,顯示出明確的文化從屬關(guān)系。此時的苴國對蜀稱臣納貢,巴蜀仍維持著既競爭又共存的平衡,三國關(guān)系處于相對穩(wěn)定的初始階段。
二、苴國親巴,三國制衡的形成
戰(zhàn)國中期,隨著各國實力消長與地緣需求變化,初始格局逐漸瓦解。苴國的政治轉(zhuǎn)向成為關(guān)鍵變量,打破了蜀強巴弱的平衡,形成“蜀苴反目、苴巴結(jié)盟”的三角博弈態(tài)勢,這一轉(zhuǎn)變本質(zhì)上是地緣利益對宗親關(guān)系的超越。
苴國的離心傾向源于多重因素的疊加。經(jīng)濟層面,蜀王對苴國的貢稅索取日益頻繁,而苴國控制的蜀道貿(mào)易帶來的財富積累,使其產(chǎn)生了擺脫蜀國控制的經(jīng)濟基礎(chǔ);民族層面,苴國境內(nèi)混居著蜀族、氐族、羌族、濮族等多個族群,蜀王通過“羈縻府”實施間接統(tǒng)治,客觀上培育了苴國的獨立意識;政治層面,蜀王杜尚的分封本就暗含“疏解王室矛盾”的意圖,隨著蜀國王位更迭,苴侯與蜀王的宗親紐帶逐漸弱化。至開明十一世時期,苴國已不再滿足于藩屬地位,轉(zhuǎn)而尋求外部盟友以抗衡蜀國。
巴國成為苴國的天然盟友。巴蜀長期因疆域爭奪與資源分配存在沖突,《華陽國志》明確記載“巴、蜀仇也”,巴國始終尋求制衡蜀國的力量。苴國的倒向恰好彌補了巴國的軍事劣勢,兩國很快形成抗蜀同盟。公元前4世紀中后期,苴國聯(lián)合巴國在蒼溪歧坪鎮(zhèn)發(fā)動“閬中之戰(zhàn)”,一度切斷蜀國北上糧道,顯示出聯(lián)盟的實戰(zhàn)效力。此時的苴國疆域已擴張至鼎盛,涵蓋今四川廣元大部、綿陽梓潼及陜西寧強等地,其出土陶器兼具蜀文化繩紋與巴文化方格紋特征,成為兩國結(jié)盟的物質(zhì)佐證。
蜀苴關(guān)系則徹底走向破裂。面對苴巴同盟的威脅,蜀國采取經(jīng)濟制裁與政治施壓,但礙于苴國的戰(zhàn)略價值與宗親關(guān)系未立即動武,僅以“秦兵至,自退之”的表態(tài)警示苴侯。這種隱忍進一步堅定了苴國的反蜀立場,三國形成兩兩牽制的三角格局:蜀國雖強,卻面臨苴巴同盟的南北夾擊;苴巴聯(lián)盟依賴彼此力量對抗蜀國,卻缺乏真正的信任基礎(chǔ);地緣平衡的脆弱性為外部勢力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機。
三、秦國介入與三國覆滅的共同命運
公元前316年,秦國以“石牛糞金”的計謀為契機,發(fā)動軍事進攻,徹底打破西南地緣平衡,巴、蜀、苴三國在短短一年內(nèi)相繼覆滅,其命運轉(zhuǎn)折成為戰(zhàn)國時期“遠交近攻”戰(zhàn)略的典型案例。
秦國對西南的覬覦已久,但其擴張始終受制于蜀道天險。蜀王杜蘆(開明十二世)時期的內(nèi)政失誤為秦國提供了突破口:這位年輕君主在擊敗巴國后,決意討伐苴國以重塑權(quán)威,不僅拒絕群臣進諫,還征調(diào)“五丁力士”開鑿蜀道以方便進軍。秦惠文王順勢采納張儀之計,制作五頭“能屎金”的石牛,假意贈予苴侯,誘使蜀國全力修筑金牛道。這條寬3-5米的棧道貫通后,秦國軍隊沿金牛道南下的距離縮短至120公里,天險不復(fù)存在。
戰(zhàn)爭進程呈現(xiàn)“借道滅蜀、順手吞苴、乘勢滅巴”的連鎖反應(yīng)。當(dāng)蜀軍北上伐苴時,苴侯緊急向秦國求援,張儀、司馬錯率軍以“援苴”為名進入苴國,卻在苴侯開城迎接后突襲蜀軍。由于金牛道已為秦軍控制,蜀軍退路被斷,迅速潰敗,蜀王戰(zhàn)死,太子被俘。秦軍滅蜀后,以苴侯“引狼入室”為由廢黜其位,順勢吞并苴國,吐費城的戰(zhàn)國城墻雖有8米寬的夯土基座,卻未能抵御秦軍攻勢,48小時內(nèi)即告淪陷。此時的巴國剛經(jīng)巴蜀之戰(zhàn)元氣大傷,面對秦軍兵鋒毫無抵抗能力,很快被秦國納入版圖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明確記載:“(秦惠文王)九年,司馬錯伐蜀,滅之。貶蜀王更號為侯,而使陳莊相蜀。蜀既屬秦,秦以益強,富厚,輕諸侯。”
三國覆滅的根源在于內(nèi)部矛盾與外部戰(zhàn)略的雙重作用。蜀王的剛愎自用、苴侯的短視投機、巴國的實力孱弱,使其難以形成抗秦合力;而秦國則精準(zhǔn)利用三國矛盾,以最小成本實現(xiàn)了“得蜀則得楚,得楚則天下并矣”的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。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印證了這一結(jié)局:廣元中子鋪遺址出土的晚期器物中,蜀文化與苴國特色器物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秦式方格紋陶器,標(biāo)志著秦國對該區(qū)域的有效控制。
四、歷史余韻:三國關(guān)系的地緣啟示與文明遺產(chǎn)
巴、蜀、苴三國的興衰史不僅是西南地區(qū)的區(qū)域敘事,更折射出戰(zhàn)國時期地緣政治的普遍規(guī)律,其文明遺產(chǎn)也深刻融入中華文明的發(fā)展脈絡(luò)。
從地緣戰(zhàn)略視角看,三國關(guān)系的演變揭示了“弱國無外交”與“平衡易破”的殘酷邏輯。苴國試圖以“聯(lián)巴抗蜀”打破藩屬地位,卻最終淪為秦國的“戰(zhàn)略跳板”;巴國寄望借秦國之力制衡蜀國,反而加速自身滅亡;蜀國因內(nèi)部權(quán)力斗爭與決策失誤,喪失了數(shù)百年積累的文明優(yōu)勢。三者的悲劇印證了司馬遷“以權(quán)利合者,權(quán)利盡而交疏”的論斷,也為后世區(qū)域政權(quán)的外交策略提供了鏡鑒。
從文明融合視角看,三國的短暫博弈促進了西南地區(qū)的文化交融。苴國作為蜀、巴、秦文化的交匯點,其出土的青銅劍兼具楚式劍首與巴蜀符號特征,船棺葬與石板墓的共存現(xiàn)象則見證了多民族的生活融合。秦國滅三國后,在蜀地設(shè)蜀郡,在苴國故地置葭萌縣,將中原郡縣制推行至西南,蜀錦技術(shù)、鹽業(yè)管理與中原農(nóng)耕經(jīng)驗相互借鑒,為漢代西南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濟繁榮奠定了基礎(chǔ)。
從歷史進程視角看,三國覆滅是秦漢大一統(tǒng)的重要鋪墊。秦國通過吞并巴、蜀、苴,獲得了豐富的糧食與兵源,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記載“蜀既屬秦,秦以益強,富厚,輕諸侯”,其財富與人力支撐了秦國后續(xù)對六國的戰(zhàn)爭。同時,金牛道等交通設(shè)施的完善,打破了西南與中原的地理隔絕,使“天府之國”真正融入中華文明體系,為后世中央政權(quán)治理邊疆提供了范本。
五、結(jié)語
巴、蜀、苴三國的關(guān)系演變是一部濃縮的西南地緣政治史。從蜀苴同源的分封初始,到苴巴結(jié)盟的關(guān)系裂變,再到三國覆滅的共同結(jié)局,其每一次關(guān)系轉(zhuǎn)折都緊扣地緣利益的核心邏輯。文獻記載的“石牛計”與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器物遺存相互印證,還原了這段被塵封的歷史:三國既創(chuàng)造了獨特的區(qū)域文明,又因內(nèi)部紛爭錯失了自主發(fā)展的機遇,最終成為秦國統(tǒng)一大業(yè)的墊腳石。
這段歷史不僅揭示了戰(zhàn)國時期諸侯爭霸的殘酷法則,更彰顯了中華文明“多元一體”的發(fā)展路徑——巴人的勇武、蜀人的智慧、苴人的兼容,最終在秦漢大一統(tǒng)的框架下融為一體,成為中華文明多樣性與統(tǒng)一性的重要見證。而金牛道上的斑駁遺跡,至今仍在訴說著那段關(guān)于權(quán)力、博弈與融合的古老故事。
(作者簡介:道堅,羌族,大理醫(yī)學(xué)院畢業(yè),詩人、作家,重慶市九龍坡區(qū)人大代表、曾任北京大學(xué)、清華大學(xué)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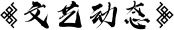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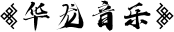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