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董小玉、廖仕杰
在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的地理版圖上,作家喬葉始終以勘探者的姿態(tài),執(zhí)著地叩擊著時代精神的礦脈。她憑借扎實(shí)的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筆觸,對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,精心構(gòu)筑起一系列具有深刻社會內(nèi)涵的文學(xué)佳作。《寶水》是她多年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探索的結(jié)晶,作品以豫北小鎮(zhèn)為原點(diǎn),用平靜而透亮的敘事,將鄉(xiāng)土的呼吸、時代的風(fēng)聲與人的靈魂交織在一起。當(dāng)我們將目光投向?qū)毸迥切└矟M青苔的屋脊時,會發(fā)現(xiàn)檐角滴落的不僅是晨露,更是一個民族在現(xiàn)代化進(jìn)程中的精神震顫。

鄉(xiāng)村敘事的詩意波瀾
喬葉的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不以沖突取勝,而以靜水流深的方式展現(xiàn)矛盾。她善于在細(xì)膩入微的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描寫中植入深邃的敘事張力,使看似平凡無奇的故事?lián)碛袕?qiáng)大的沖擊力。這種獨(dú)特的寫作手法,既有沈從文《邊城》中地方生活的詩意,又與愛麗絲·門羅筆下日常中情感爆發(fā)的瞬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
鄉(xiāng)建專家孟胡子,認(rèn)為“長安不是客,就當(dāng)自家過”,一瓶“懷川醉”是他出入各家的通行證。這是一個順應(yīng)時代潮流、扎根鄉(xiāng)村干實(shí)事的時代新人。其中賣粉條的描寫極具典型性。他堅持用祖?zhèn)髀┥字谱魇止し蹢l,卻在包裝箱印上二維碼追溯生產(chǎn)流程。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在此刻碰撞:漏勺劃出的弧線延續(xù)著千年農(nóng)耕文明的肌理,二維碼的幾何線條則編織進(jìn)數(shù)字時代的經(jīng)緯。這種敘事手法,與汪曾祺《受戒》以小和尚明海的眼睛看世俗類似,卻在當(dāng)代語境中生長出新的美學(xué)維度。
喬葉寫鄉(xiāng)土,如沈從文般以克制表達(dá)情感,以溫情凝視人性。不同的是,她筆下的鄉(xiāng)土不是被時間遺忘的邊地,而是被現(xiàn)代化卷入的“中間地帶”。她不歌頌,也不哀嘆,只是冷靜地凝視這種變化帶來的不安,平靜地記錄那種懸而未決的搖晃。而這正是當(dāng)代中國許多“小鎮(zhèn)”共同的心理底色。
勾勒活色生香的人物
《寶水》里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(jié),只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:手藝人、村醫(yī)、返鄉(xiāng)青年、基層干部等。小說中的主角鄉(xiāng)村女干部大英,其言行都透著一股子潑辣勁兒,受到委屈時可以當(dāng)眾扇對方的耳光,而面對自己的拐腿丈夫與抑郁女兒,則表現(xiàn)出柔情天真的一面。在生活中,喬葉讓這些人物既各自掙扎,又彼此照亮。
在祠堂被改造為“鄉(xiāng)村記憶館”的情節(jié)里,老文書的賬本與95后村官的電子表格并列展示,成為當(dāng)代鄉(xiāng)村的縮影。傳統(tǒng)秩序在數(shù)字時代被重新定義,而“記憶”成了一種需要被設(shè)計和策展的文化資源。喬葉沒有直接評判這種變化,而是讓場景本身說話:老紙張的紋理、LED燈的冷光、村民略顯尷尬的笑容,共同構(gòu)成了現(xiàn)實(shí)的版圖。
書中返鄉(xiāng)青年小凱在直播帶貨時突然改用方言喊麥,那一瞬間,商業(yè)邏輯撞上鄉(xiāng)土記憶,是那么的自然鮮活。而老村醫(yī)反復(fù)擦拭聽診器,像在擦拭一個即將消失的過往,他用身體化的抵抗,捍衛(wèi)一份瀕危的尊嚴(yán)。這種細(xì)微的掙扎,讓小說充滿溫度,也讓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重新長出血肉。
這種細(xì)微的人物刻畫,讓讀者在寶水之地看到自己的身影,喚起一種情感的共鳴。正如卡爾維諾在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所說:“每個城市都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地點(diǎn),而是人類情感的交匯港灣。”喬葉筆下的“寶水”,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鄉(xiāng)村小鎮(zhèn),更是現(xiàn)代社會中無數(shù)個村莊的生動縮影,折射出每個人在社會體系中的身份定位和精神困境。
難以走出的故鄉(xiāng)情結(jié)
透過寶水的日常,我們看見的是整個中國轉(zhuǎn)型的陣痛。小鎮(zhèn)看似風(fēng)平浪靜,在現(xiàn)代化浪潮中發(fā)生著深刻變化。這種變化既體現(xiàn)在價值觀的悄然更迭上,也反映在人與人關(guān)系的重新構(gòu)建之中。
《寶水》因此也超越了單純的個人故事范疇,成為一部新山鄉(xiāng)巨變的社會學(xué)樣本。小說中新村民與原住民的碰撞構(gòu)成社會變遷的微觀鏡像:一方面,當(dāng)主人公夫婦帶著城市資本入駐寶水村開辦民宿,二嫂等原住民既渴望通過合作獲得經(jīng)濟(jì)收益,又警惕著外來文化對鄉(xiāng)村倫理的瓦解。這種“既要現(xiàn)代化紅利,又怕丟失傳統(tǒng)”的集體焦慮,具體化為民宿改造時對老宅門楣的爭執(zhí)——城里人要落地窗追求美感,老木匠堅持榫卯結(jié)構(gòu)承載著家族記憶。而當(dāng)城里來的建筑設(shè)計師堅持“修舊如舊”時,村民老栓頭卻偷偷用水泥抹平了祖屋的夯土墻——這個看似背叛傳統(tǒng)的舉動,實(shí)則是底層民眾對現(xiàn)代性最樸素的擁抱。讓傳統(tǒng)活在當(dāng)下,這也是寶水村的智慧。他們保留“祭河神”儀式,卻將其轉(zhuǎn)化為非遺展演;傳統(tǒng)社火道具被制成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,但耍社火的童子必須從本村學(xué)生中選拔。這種“傳統(tǒng)的發(fā)明”,印證了霍布斯鮑姆關(guān)于文化重構(gòu)的理論,也為鄉(xiāng)村振興提供了文學(xué)注腳。
《寶水》在質(zhì)樸中見深意。喬葉用細(xì)密的針腳,繡出個體命運(yùn)的紋路,也鋪開時代變遷的圖景。小說中九奶奶的話令人刻骨銘心:“人在人里,水在水里,活這一輩子哪能只顧自己”,這可以說是本書的“魂魄”。它道出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幫襯,同時也要替他人著想的胸襟與情懷。本雅明在《發(fā)達(dá)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》中所說:“城市、鄉(xiāng)村、街道、房屋……它們既是現(xiàn)實(shí)的物質(zhì)存在,又是富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。”寶水就是這樣的地方——它是喬葉筆下具體的小鎮(zhèn),也是每個人心中或遠(yuǎn)或近的故鄉(xiāng)。它見證了個體的悲歡離合,也折射著社會的滄海桑田。而喬葉的文字,則如同一束溫暖而又犀利的光,帶領(lǐng)我們在這片小鎮(zhèn)的土地上,看見自己的故鄉(xiāng),也洞察世間的萬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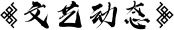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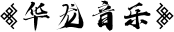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