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八十載風(fēng)雨滄桑。10月10日-10月17日,“戰(zhàn)火中的文藝先鋒——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文藝界重慶歷史名人展”在江北嘴中央商務(wù)區(qū)中央公園開(kāi)展。這場(chǎng)展覽不僅是對(duì)歷史的回望,更是對(duì)文藝精神的傳承。循著郭沫若、老舍、冰心、徐悲鴻、張書(shū)旂、陽(yáng)翰笙、陳白塵、曹禺等41位文藝先鋒的足跡,走進(jìn)那段以筆為槍、以藝鑄魂的歲月,感受他們用生命點(diǎn)燃的民族火炬,在歷史回響中汲取新時(shí)代文藝力量。
——題記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的一個(gè)霧晨,日軍轟炸機(jī)的轟鳴聲撕裂重慶的天空。在嘉陵江畔的防空洞里,徐悲鴻借著煤油燈的微光,完成了《巴人汲水圖》的最后一筆。那些在懸崖邊負(fù)重攀登的身影,不僅是山城挑夫的寫(xiě)照,更是一個(gè)民族在戰(zhàn)火中不屈的隱喻——“他們背著整個(gè)中國(guó)的希望。”徐悲鴻在日記中如是寫(xiě)道。
這是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大后方文藝界的真實(shí)縮影。山河破碎,鐵蹄縱橫,一群文藝先驅(qū)將重慶變成了另一個(gè)戰(zhàn)場(chǎng)——一個(gè)以筆墨為槍炮、以舞臺(tái)為壕塹的精神防線。在最黑暗的歲月里,文藝不僅是慰藉,更是武器;不僅是記錄,更是抵抗。
文心劍膽:文學(xué)家的悲歌與怒吼
在老舍位于北碚的寓所“多鼠齋”中,老鼠常在夜間啃咬書(shū)稿。這位文學(xué)大師一邊驅(qū)趕老鼠,一邊完成了《四世同堂》的創(chuàng)作。他的夫人胡絜青帶著三個(gè)孩子,徒步兩個(gè)多月從北平逃到重慶,沿途目睹的民間苦難,悉數(shù)化作老舍筆下鮮活的細(xì)節(jié)。在1944年的一次文藝界集會(huì)上,老舍動(dòng)情地說(shuō):“我們要用筆記錄下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血與淚。”
茅盾在唐家沱的陋室中寫(xiě)下《白楊禮贊》,感嘆道:“白楊不是平凡的樹(shù),它在西北極普遍,不被人重視,就跟北方的農(nóng)民相似。”這篇文章成為抗戰(zhàn)文學(xué)的精神旗幟。冰心在歌樂(lè)山上的“潛廬”繼續(xù)《再寄小讀者》的寫(xiě)作,以溫柔的筆觸告訴孩子們:“這世界雖有戰(zhàn)爭(zhēng),但更有愛(ài)與希望。”
張恨水的《八十一夢(mèng)》在《新民報(bào)》連載時(shí),因尖銳的諷刺屢遭刪改。他自序中寫(xiě)道:“這些夢(mèng),有的被檢查官剪掉翅膀,有的被現(xiàn)實(shí)磨鈍鋒芒,但它們都是時(shí)代的見(jiàn)證。”
最震撼的是郭沫若的歷史劇《屈原》。1942年4月3日,重慶國(guó)泰戲院座無(wú)虛席,當(dāng)金山飾演的屈原發(fā)出“雷電頌”的咆哮:“炸裂呀,我的身體!炸裂呀,宇宙!”整個(gè)山城為之共鳴。觀眾含淚鼓掌,演員謝幕十余次。次日,《新華日?qǐng)?bào)》報(bào)道:“劇場(chǎng)里的掌聲,是最有力的抗議。”
丹青血淚:畫(huà)布上的抗?fàn)幣c希冀
徐悲鴻的《巴人汲水圖》高300厘米,卻是在防空洞里分段完成的。他回憶,“每次空襲警報(bào)解除,我就趕緊畫(huà)上一段。這幅畫(huà)是在炸彈爆炸間隙誕生的。”他的《愚公移山》借鑒印度模特的身體語(yǔ)言,講述著中國(guó)人不屈的寓言。畫(huà)中揮鎬的壯漢,目光堅(jiān)毅,成為民族精神的視覺(jué)象征。
“虎癡”張善子在聽(tīng)聞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后,嘔心瀝血?jiǎng)?chuàng)作《猛虎撲日?qǐng)D》贈(zèng)予陳納德航空隊(duì)。畫(huà)面上28只猛虎(象征當(dāng)時(shí)中國(guó)的28個(gè)行省)飛越太平洋,直撲日寇。陳納德將軍致信:“您的飛虎將永遠(yuǎn)在我們機(jī)翼上翱翔。”令人痛心的是,張善子因過(guò)度勞累于1940年病逝,臨終前仍念叨著“還要再畫(huà)一幅……”
張書(shū)旂創(chuàng)作《百鴿圖》時(shí),重慶正遭受最猛烈的轟炸。他拆掉自己的西裝口袋取白絨布作畫(huà),用家中棉被填充畫(huà)箱。當(dāng)這幅象征和平的巨作遠(yuǎn)渡重洋抵達(dá)白宮時(shí),羅斯福總統(tǒng)特意致電贊賞:“這是來(lái)自中國(guó)人民最美好的祝福。”
在金剛坡下的農(nóng)舍里,傅抱石開(kāi)創(chuàng)了渾茫深邃的“抱石皴”。他的《瀟瀟暮雨》中,狂放的筆觸仿佛要將天地間的悲憤盡數(shù)傾瀉。而李可染在同一時(shí)期的山水畫(huà)中,墨色深沉厚重,他說(shuō):“我要用最濃的墨,畫(huà)出最亮的光。”
舞臺(tái)烽煙:戲劇界的“霧季公演”傳奇
每年10月至次年5月,重慶的濃霧是天然的防空屏障,也催生了世界戲劇史上的奇跡——“霧季公演”。據(jù)史料記載,1941-1945年間,重慶共創(chuàng)作演出話劇110余部,觀眾達(dá)百萬(wàn)人次之多。曹禺的《家》在國(guó)泰戲院場(chǎng)場(chǎng)爆滿。當(dāng)張瑞芳飾演的瑞玨在風(fēng)雪中死去,臺(tái)下抽泣聲不絕。有一次,空襲警報(bào)響起,觀眾卻喊道:“演下去!我們不怕炸彈!”
吳祖光的《風(fēng)雪夜歸人》寫(xiě)盡了亂世中的人格堅(jiān)守。劇中名伶魏蓮生最終選擇離開(kāi)富貴生活,演員金山在詮釋這個(gè)角色時(shí),融入了自己從上海輾轉(zhuǎn)來(lái)渝的流亡經(jīng)歷。他在回憶錄中說(shuō):“每次演出,我都像是在與自己的靈魂對(duì)話。”
最轟動(dòng)的是陽(yáng)翰笙的《天國(guó)春秋》。劇中那句“大敵當(dāng)前,我們不該自相殘殺!”引發(fā)長(zhǎng)達(dá)數(shù)分鐘的掌聲。該劇連續(xù)加演十余場(chǎng),創(chuàng)下當(dāng)時(shí)票房紀(jì)錄。
1941年6月5日,日軍轟炸導(dǎo)致重慶大隧道慘案,數(shù)千人窒息而死。一周后,演員們?cè)跉埰频奈枧_(tái)上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白楊臉上的淚水不需要表演。演出結(jié)束后,許多觀眾自發(fā)上臺(tái)擁抱演員,場(chǎng)面令人動(dòng)容。
薪火相傳:學(xué)術(shù)與教育的堅(jiān)守
在歌樂(lè)山下的“雅舍”,梁實(shí)秋在油燈下翻譯《莎士比亞全集》。炸彈不時(shí)在遠(yuǎn)處爆炸。他在散文中寫(xiě)道:“譯完《亨利四世》的那天,一枚炸彈落在后院,把剛洗的衣服都炸飛了。幸好稿子還在。”
沈尹默在防空洞里校勘《歷代書(shū)法論》,雙目幾近失明仍不輟筆。他在給學(xué)生信中寫(xiě)道:“目可盲,筆不可停。”章士釗在簡(jiǎn)陋的茅屋里完成《邏輯指要》,將中國(guó)名學(xué)與西方邏輯熔于一爐。每當(dāng)空襲來(lái)臨,他總是把書(shū)稿藏好才去避難。
晏濟(jì)元在江津延續(xù)著中國(guó)美術(shù)的血脈。在最困難的時(shí)期,學(xué)生們用鍋底灰制墨,用青石板當(dāng)畫(huà)紙。呂鳳子在璧山興辦正則職業(yè)學(xué)校,他親自刻下學(xué)校碑文:“餓殍滿地,吾輩更當(dāng)以藝術(shù)喚醒國(guó)魂。”
音樂(lè)界同樣不屈。劉雪庵的《長(zhǎng)城謠》傳遍大后方,“四萬(wàn)萬(wàn)人齊蹈厲,同心同德一戎衣”。他的《何日君再來(lái)》雖被誤讀,卻成了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最復(fù)雜的情感注腳。1939年,在重慶舉辦的“黃河大合唱”首演中,觀眾自發(fā)站起合唱,歌聲震天,連遠(yuǎn)處的日軍俘虜營(yíng)都能聽(tīng)見(jiàn)。
永恒的先鋒:文藝精神的當(dāng)代回響
這些文藝先鋒在最黑暗的歲月里創(chuàng)造了最燦爛的文明景觀,平均年齡卻不過(guò)四十歲。胡風(fēng)主編的《七月》雜志雖然每期都是用最粗糙的土紙印刷,但發(fā)行量始終居高不下,也培養(yǎng)了大批青年作家。方敬的詩(shī)集《雨景》在戰(zhàn)火中出版,他在序言中寫(xiě)道:“我們要在廢墟上種詩(shī)。”張大千晚年回憶重慶歲月時(shí)說(shuō):“在金剛坡下,我找到了中國(guó)畫(huà)的真精神。那不是技巧,而是一個(gè)民族在絕境中依然保持創(chuàng)造力的勇氣。”1944年,他在成都舉辦“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(huà)展”,排隊(duì)群眾長(zhǎng)達(dá)兩里,卻將全部所得捐獻(xiàn)給了前線。
今天,當(dāng)我們重讀《四世同堂》、凝視《巴人汲水圖》、回味《雷電頌》時(shí),我們眼前的不僅是藝術(shù)品,更是一個(gè)民族在存亡之際的精神自傳。那些發(fā)黃的劇本、斑駁的畫(huà)布、殘缺的手稿,已經(jīng)構(gòu)成了我們民族文明史上堅(jiān)韌的一頁(yè)。
據(jù)說(shuō)重慶南山抗戰(zhàn)遺址博物館里保存著徐悲鴻用過(guò)的調(diào)色盤(pán),顏料早已干涸,但調(diào)色板上深深的劃痕依然訴說(shuō)著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力度與決絕:真正的文藝從來(lái)不是太平盛世的點(diǎn)綴,而是危亡時(shí)刻的脊梁。
在中華民族偉大復(fù)興征程上,從戰(zhàn)火中淬煉出的文藝先鋒精神,始終是我們珍貴的精神資源——它讓個(gè)人才情深度融入民族命運(yùn),在絕境中迸發(fā)創(chuàng)造勇氣,以美學(xué)力量重構(gòu)民族自信。這些文藝先驅(qū)作品,不僅忠實(shí)記錄了民族曾經(jīng)歷的苦難,更以精神之光為炬,為中華民族偉大復(fù)興指引了奮進(jìn)方向。
(作者:鄭維山,系重慶市文藝評(píng)論家協(xié)會(huì)理事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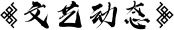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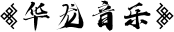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